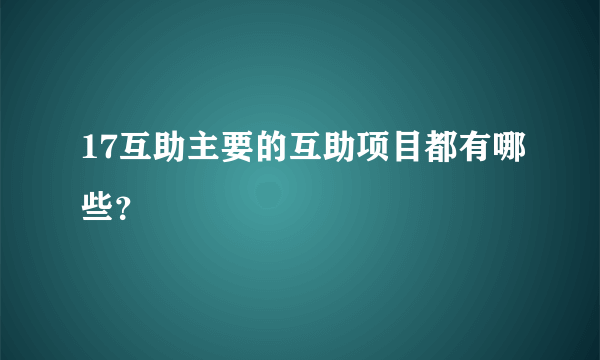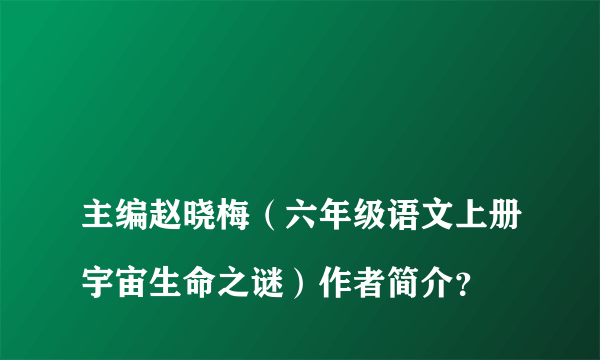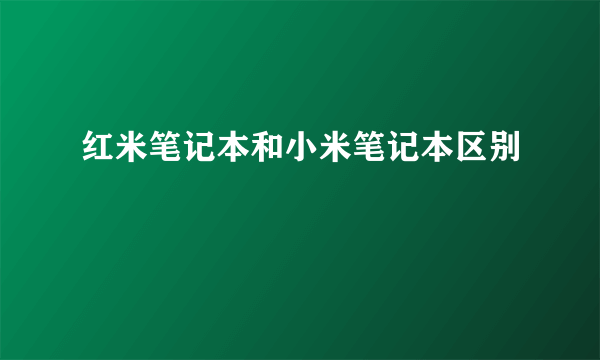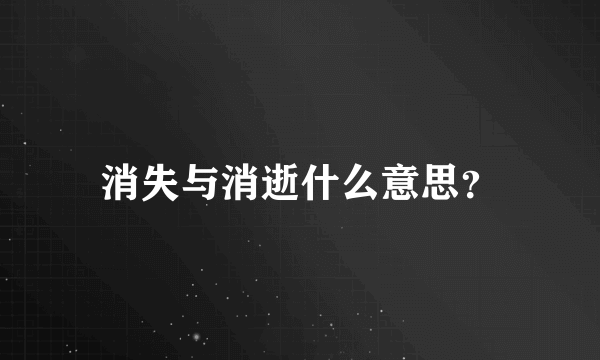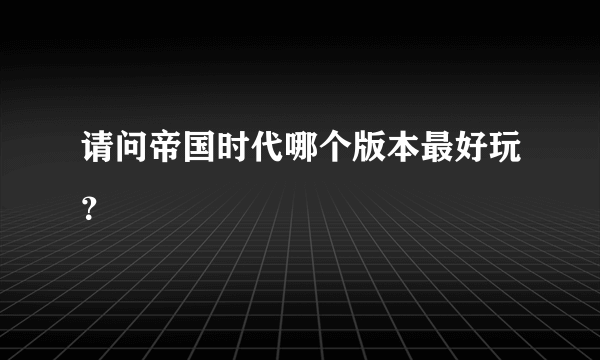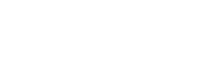"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是什么意思?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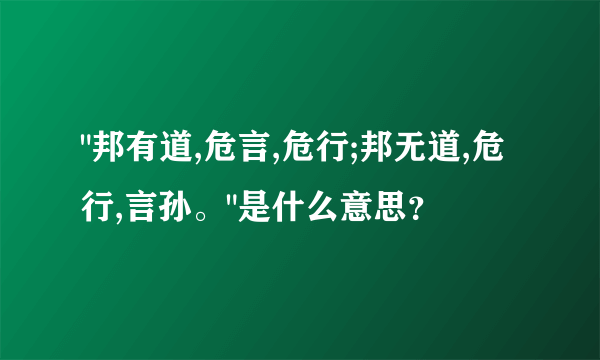
面对一个不好甚至是坏的制度,一个有责任感的个人应当如何作为?这似乎是近年来一直被津津乐道的话题。其实圣人早早对此就有过说法,“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四书章句集注云:危,高峻也。孙,卑顺也。于是我们知道“危行”不是指如暴力革命、以恶抗恶般的危险行为,而是君子不随波不媚俗的高洁品行。无论邦有道无道,“危行”都是必须的,而“危言”只能对愿意听言语的人才能发生效力,也才有必要。因此,“言孙”并不是怯懦,而只是为了确保“危行”的可能。同时,这也体现了传统儒家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在言语与行为之间,更重视行为及其后果。而这个“危行”,自然也包括不同流合污的“不作为”。 然而孔子的这段话,尤其是后半部分,如今却常被一些慷慨激昂的批评家引以为中国人圆滑与怯懦的证明。他们觉得“言孙”就是说话装孙子,这怎么可以呢?起码要像个老子。于是,仿佛老大中国一下子冒出了无数“真的猛士”,我们如今经常可以观看到一些激烈的“危言”,以及对于中国的种种弊端痛心疾首的斥责。但是再仔细一看,却发现借着互联网与大众媒体娱乐的掩护,这些“危言”非但没有危及这些批评家现实的生活,反倒可以换来宣泄感、喝彩声、稿费以及高点击率。于是,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不是我们的社会,而是这些批评家自己,在骂与被骂中日益显赫起来。 最近学界有两件“不作为”的“危行”,其掀起的热浪,却也可以拿来和之前诸多批评家“危言”的效果相参照。一是清华的陈丹青辞职,一是北大的贺卫方公开拒招硕士生。 在研究生招生制度利弊这个问题上,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但贺、陈两位先生的不同在于,他们并没有疾言厉色地要打倒什么、重建什么,他们只是宣布退出,退出这个不合理的招生游戏制度。从博客中国对贺卫方教授的访谈里,我们可以看到马丁·路德·金倡导“公民不服从”的隐约印迹,也可以看到耶林“为权利而斗争”的现实影响。这种公民权利,也就是“不作为”的权利,用以赛亚·柏林的话来讲就是“消极自由”的权利,即我有做什么的权利,同时我还拥有不做什么的权利。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中,这种“不作为”权利在政治领域的运用,可以从圣雄甘地、托尔斯泰、英国费边主义者一直追溯到瓦尔登湖畔自食其力的哲人梭罗。但是,在有这么多西方思想撑腰打气的鼓舞下,我们却也可以惊讶地发现,咦,这不正是孔子所说的“危行言孙”? 所以,其实都犯不着扯上那么多洋大人,也同样可以在中国思想里看到现成的这么两条道路。你要是觉得这社会还有救,你就可既“危言”纠弊又“危行”正己;你要是觉得这是个烂摊子,你只要以“危行”正己就可以了,发牢骚也没用。贺陈两位先生便是如此行事的,这就足以令我们尊敬。但问题是,却还有众多看客总盼望着第三条道路,即在自己“行孙”的同时,还做着“危言”治国的美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