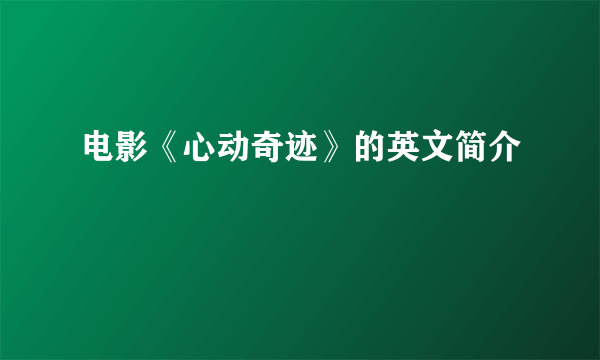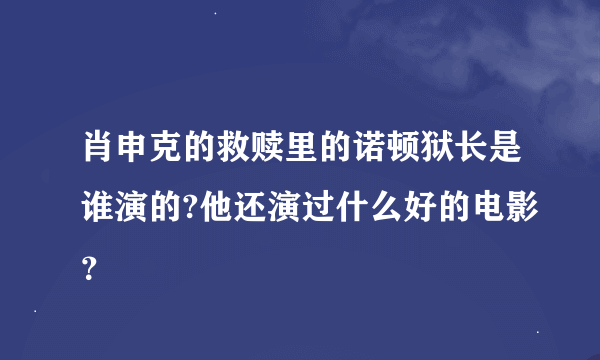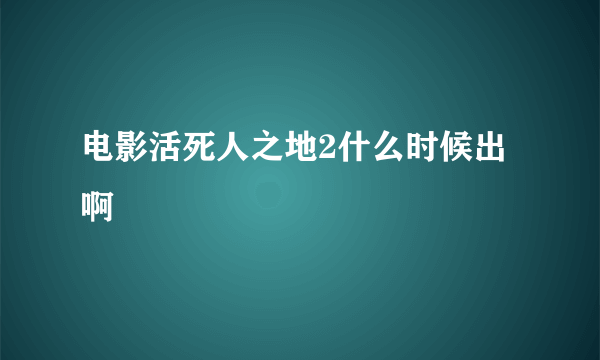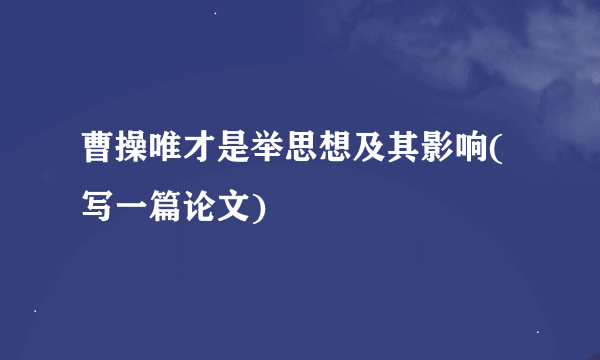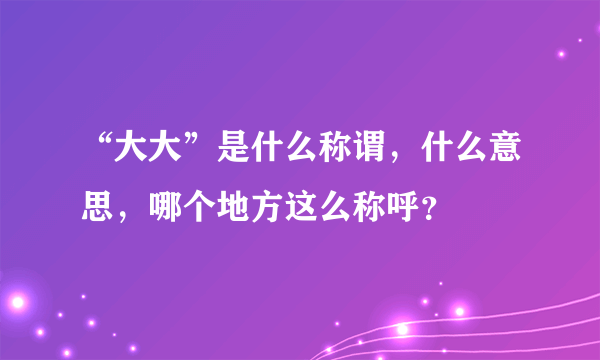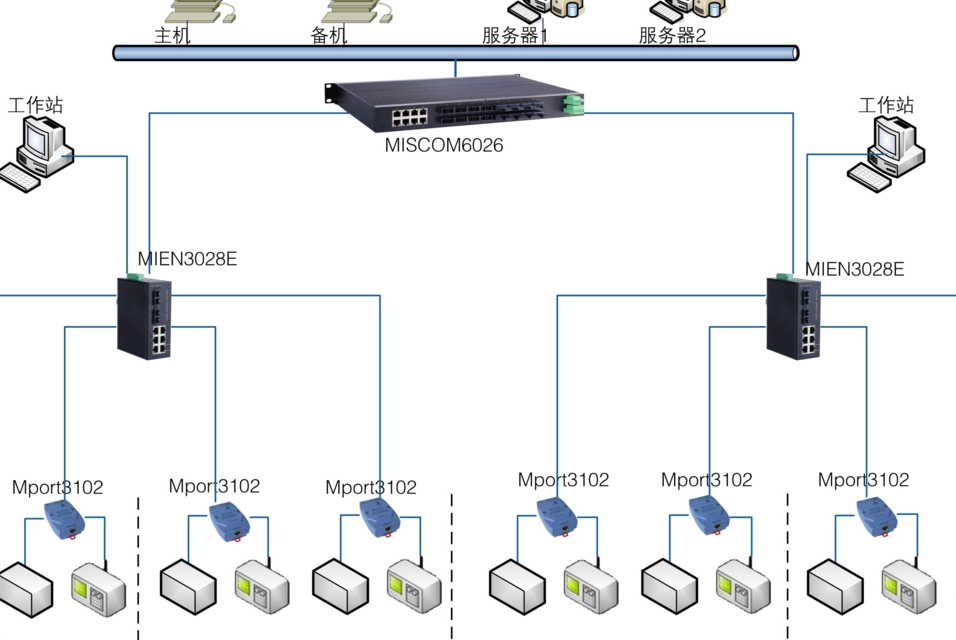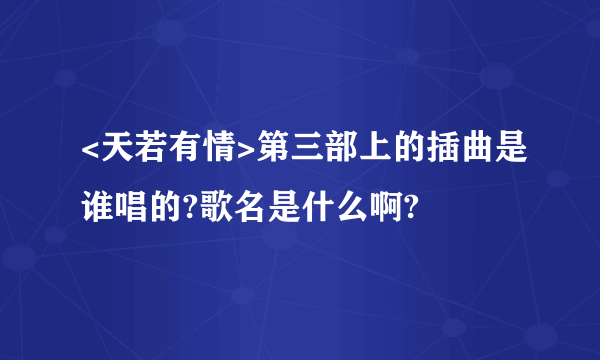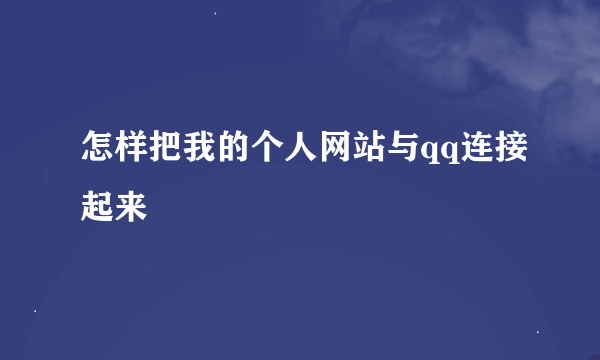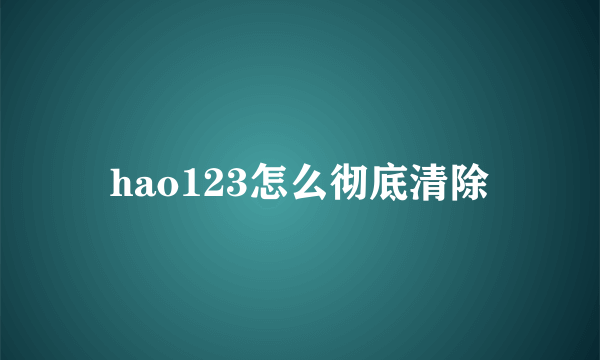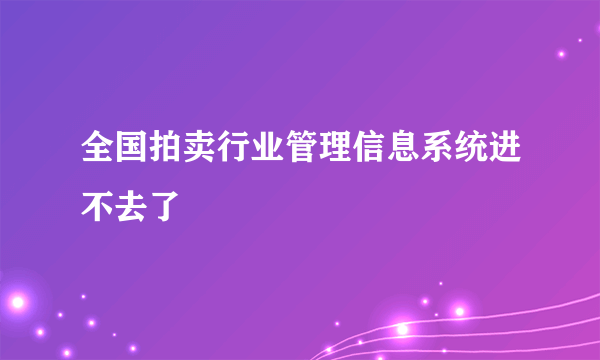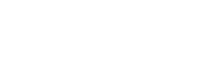《我十一》电影观后感怎么写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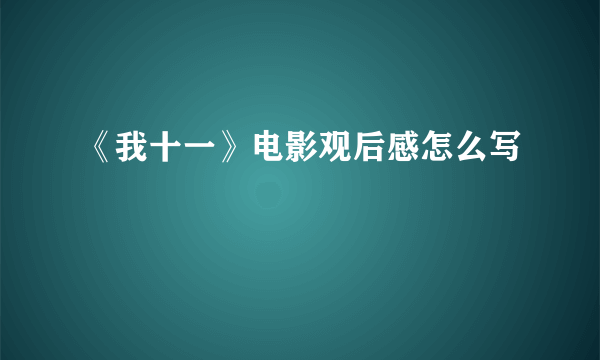
每个人都会被一些早年记忆牢牢纠缠,不管走到何处,境遇如何变化,那些回忆总能轻车熟路地迎头赶上。在饭桌上,在旅途中,在各种漫不经心的瞬间,让人彻底穿越。反反复复的穿越之中,往事被不断重塑,片断延伸成段子,段子里生长出故事,突然就有那么一天,你发现自己竟有过一段惊心动魄的成长史。若恰巧你是个小文青或老文中,这些纠缠变幻的往事便有了着落。当创作者被往事追赶,唯有写下来,与往事干杯,方可释怀。 对于少年往事,王小帅依然视若珍宝。《我11》讲述了少年王憨在文革结束前一年的生活,红领巾、白衬衫,大喇叭,课间操,大红标语,毛主席像,玻璃球,捉迷藏,邻里唠家常,哥哥打群架……私人记忆的场景在各种年代背景声里逐一展现,个人回忆与集体记忆在这部电影里交织一片。从《青红》到《我11》,王小帅力图还原时代记忆,用电影致敬时代,更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类似这样的创作并不少见。同样成长于文革期间的作家林白,90年代写出《一个人的战争》,深度涉及时代事件与少女私人记忆。与林白同时期的陈染在小说《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中,也都夹杂着不少个人记忆。电影方面,台湾有侯孝贤的《童年往事》,香港则有罗启锐的《岁月神偷》。 小说掠过不提,来说说电影。《童年往事》、《岁月神偷》与《我11》三部电影,大概都算是半自传式的,讲述的故事基本忠于作者的早年记忆。除了恰好为台湾,香港、大陆三地,三部影片各自的时间跨度也挺有意思。数迅侯孝贤生于1947年,《童敬老年往事》大致跨越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罗启锐生于1953年,《岁月神偷》讲述的童年在60年代末。王小帅生于1966年,算是“文革之子”,《我11》的故事发生在1975年。 无论讲述外省移民少年成长的《童年往事》,还是潜入永利街上鞋匠一家的《岁月神偷》,都有着和《我11》同样的薯稿此特质:集体记忆与个人往事的交织。这样的表现在此类题材中是必然的,也是成为一部打动观众的好电影所必须的。不同的是三部电影对这些内容表现的处理方法。 《童年往事》讲述了阿孝从幼年到青年的成长,其间经历了父亲、阿婆和母亲的去世,阿姐结婚,兄长离家。影片以平静的写实舒缓讲述这些个人往事,情感极其节制。虽然开篇就以旁白道出这是个人往事,全片叙述却始终保持冷静的注视,几乎所有的场景都以第三者的视角旁观,即便亲人离世的几场戏,也没有什么情绪上的铺陈。随着主人公成长的故事,影片对早期台湾民众集体记忆中的风光有各种描写,嘉义旧监狱旁的居民区,日式建筑,市井街道,郊野风光和乡间小路,都真实再现了那个时代的气息。细节方面处理的也很用心,父亲的椅子,书桌,旧照片,一家人合影,街边的小吃,小孩口中的“反攻大陆”。除了“我”之外的人物也在按时序展开的叙述中丰满起来,父亲坐在椅子上沉默的形象,阿婆拎着包袱走在“回大陆的路”上,无一不是既埋藏在导演内心又感染一代人的画面。在这种保持距离的叙述中,个人情怀与时代记忆完美融合。这就使《童年往事》有了超越时代的美感和情怀,即使对台湾那个时代完全不了解的人,也能在影片里感受到一代异乡人的哀愁与青春情怀。 《岁月神偷》则充盈了饱满的情感,乐观奋进不认输的香港精神是影片个人情结与时代气息的结合点。影片中,哥哥与父母是真正的主角,是私人记忆,也是时代象征。永利街上的邻里生活还原了年代场景,街头不分你我的集体晚餐,刁横的英国警察,屋顶上的教室,还有那首《I wanna be free》。不同于侯孝贤的对往事的平静注视,罗启锐的叙述中,情感满溢。“做人,总要信”,“一步难,一步佳”,励志台词的设计贯穿全片,哥哥的爱情和白血病也在起起落落的讲述中进行。这种催泪的拍法有一定风险,所幸的是,电影对细节的关注,演员的精湛演绎,使得汹涌的情感并未流于乱煽。若《童年往事》是可一再细品的茶,《岁月神偷》便是一次性灼烧喉头的酒。 《我11》的精彩在于年代图景的真实还原。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高层对美帝抱有极其强烈的戒备心,担心随时可能爆发战争。于是,在中国西南地区秘密建设一批军工厂,开展大规模国防科技建设。1966年,刚刚出生的王小帅随父母从上海迁往贵阳山区,支援三线建设。这些从大城市迁来的工厂自成一体,与外界隔绝,王小帅的童年便是在“厂”里度过。工厂,就是他的社会。当时,很多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些工厂在做什么,只知道来自北京的命令要求把工厂挪到山区,并带来了一工厂的城里人。一批来自一线城市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不知何时到头儿的新生活,一代“文革之子”就在工厂里成长。王小帅1979年才离开贵阳,整个童年和青春期在工厂里度过,那些年成为纠缠他一生的记忆。 《我11》还原的1975年三线工厂就是那批60年代人的集体记忆。故事以“我”的视角展开,热情地展现往事中的一副副画面,父亲上班,母亲做饭,集体操,玻璃球,玩双杠,被罚站,更不用说反复强调的标语和口号。核心故事是“我”与白衬衫引出的逃犯事件,又以逃犯事件引出以谢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家庭在支援三线中的悲剧命运。或许,称之为“核心事件”并不合适。逃犯事件和谢家人的悲剧在“我”那一年的成长中只是各种情结中的一条线索。导演试图将更多集体记忆中的场景——比如来势汹汹却草草收尾的械斗——穿插在故事线索中,却不够冷静,缺乏足够的叙事逻辑,主角之外的人物都面目不清。结果就是,情感意犹未尽,故事半遮半掩。整部影片略显寡淡,好似一卷带着时代印痕的相册,让人萌生感叹之情,却难以品出隽永之味。 在对往事的叙述中,集体记忆往往是符号化的。声音,图像,场景,对白。如何将这些符号自然融入叙事极其重要,设置过简可能令背景失真,强调过重则产生堆砌感。个人记忆的描绘需要必要的距离,过于贴近往事的情绪反而会有矫作之感。在我看来,对回忆最好的艺术处理是旁观式的虚构,既能理性推进叙事,亦有可能发掘更多隐匿的细节。 更好地隐藏自我,才能更好地表现自我。 飞电影院